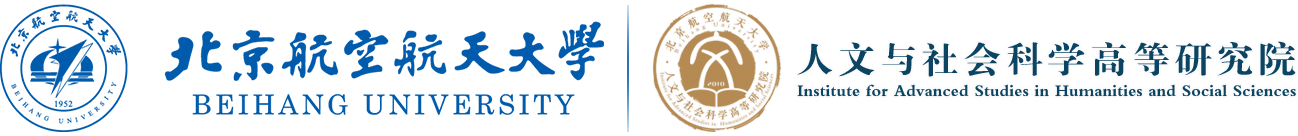高全喜:通识教育与文化自觉
□周绍纲
教育这一个关乎个人生活品质与国家命脉的制度,在现代性处境中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通识教育基本上是针对教育专业化、功利化等现代性问题设计的。中国正处于大国崛起时期,对国民的教育显然不能仅限于专家和技术工人的层次,如何培育一种健全的自由的人格,抑或培养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传人?民族的政治成熟和思想成熟需要以合乎文明标准的通识教育为前提。在国内高校探索通识教育的改革潮流中,由高全喜教授主导和设计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识教育改革颇具特色。其实践源于对国外通识教育理念、操作模式的相对完整的理解以及对国内众多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调研与比较。由此,本刊专栏走访了高全喜教授。
为什么要搞通识教育
周绍纲:近几年来通识教育在中国逐渐兴起,其中有哪些原因呢?
高全喜:首先是因为专业的分化。学科专业的分化日渐繁琐,这就使得对人才的造就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片面性。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总的来说是日渐狭隘和片面。比如文学,文学课程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再细化,有李白、杜甫、曹雪芹……,那可开的课程就太多了。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史哲、政经法,一路下来,到博士要学十年,学的确实是越来越精。但这个社会,第一未必需要这么精的人才,第二这个精非常狭窄,没有一个稳固的通识基础使得你更好地成长,将来你除了成为杜甫专家,或者搞文学研究,剩下的你都不会干。我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一波又一波的学生,现在大家明显感到,无论是学生自己还是学校的老师,还是学校的管理机构,都感觉专业分化过于细致、过于狭窄,限制了本来在大学这十年可以充分的既是非常的广博又是非常专业的、多元化知识学习。这是为什么通识教育最近这些年在中国兴起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现在的教育以专业知识为导向,知识功利主义。所谓的大学就是贩卖知识,到大学就是学知识。真正的大学应是塑造人才、塑造心灵、塑造人格的“全面的人”的培育过程。我们现在的大学除了贩卖知识之外,什么都不会,甚至有些知识乱七八糟,没多少价值。剩下的就是政治思想教育。据说你们到了大学一般就几块内容,一块就是老师贩卖知识,第二块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第三块就是私人生活——谈恋爱。这些根本不是大学所要塑造的东西。大学真正要实施的是德性教育。真正的德性教育不是政治洗脑,不是灌输意识形态,而是要培养人的自由人格、人的美德、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对真正拥有知识和健全人格的人的塑造。而这个塑造是不可能通过我们现在那么多的政治课程来实现的。随着生命的成长,人肯定要有对社会的认识,要有对生命的认识,要对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和一些人组成一个群体、参与社会,社会是什么、国家是什么、外部世界是什么等等,有所认识。这些东西是由谁来告诉你们呢?哪有这样的课程呢?专业课都是在贩卖知识嘛。文学或经济学从来都不会告诉你,你要有独立的人格,要有公民意识、国家意识。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你在大学受了十年教育,博士毕业之后,你连什么是民主法治、什么是自由人格,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你享有的权利、应承担的责任等方面都没有相关的知识,这样的教育不是很片面吗?上述就是我认为要搞通识教育的两个原因,在中国尤其如此。
周绍纲:有些人认为通识教育就是通才教育。
高全喜:现在大家都误解通识教育,对通识教育进行打包捆绑,挂上通识教育的名字似乎就时髦了。通识教育,一般人理解为通才教育,就是除了自己专业之外多学一些文史哲、政经法甚至琴棋书画,文史知识多学一些,长点见识,所谓人文素养,这就是通识教育。其实这完全是对通识教育的误读。我有个画家朋友吴为山,专门给杨振宁做了雕塑,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杨振宁会谈钢琴没错,但是弹钢琴只是他表现出来的你也看到的,通识的核心东西不是在会弹钢琴,他可能还会书法呢。哪一个科学家学了琴棋书画就成了杨振宁?那些东西都是通识的外在表述,也可能他喜欢打麻将呢。梁启超就喜欢打麻将。打麻将也不影响他成为民国时期的大学问家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通识教育。
周绍纲:在您看来,通识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
高全喜:就我理解的通识教育,或者说不光是我理解,是西方的真正的、主流的通识教育。它的核心课程不多,因为它培养的是一个健全的自由的人格,这是通识教育最主要的一个内容。人类文明几千年下来可以说真正能够培养自由健全人格的经典性的著作不会太多。从西方来说,就有两个重要的时期。一个就是古典时期,古希腊、罗马时期,那时候产生了一大批所谓轴心时代的人类文明的经典。再一个就是十五世纪之后近代的一些经典著作。近代是现代社会的早期发轫时期,那时有一批伟大的思想家。比如大家知道的牛顿、洛克、卢梭、黑格尔、康德、亚当·斯密、孟德斯鸠这批人。西方人类文明史上两个最灿烂的时期留下了一些最经典的著作。这是通识教育第一层次的核心内容。当然,这样的著作也很多,可能每个时期有那么几十本经典的专著。我们的通识教育课程安排随着规模、讲课的老师、以及学习时间的长短而不同,十年的时间你就可能多学一点通识教育,两三年的通识教育你就可能少学一点。但它主要学的就是这些经典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经典著作不是专业知识性的,很难把它们归到哪一类的知识。比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你能说它纯粹是经济学著作吗?它里边有政治学、法学、道德学的内容,它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我经常说它是元学科,是知识的知识,产生知识的元知识。古典时期也是这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知识吗?是,它们的那些知识我们现在来看都要过时了,但为什么要读它们?它们背后体现了一些基本理念、基本精神,那些知识塑造了当时的希腊人、雅典人。那时候的人是一个公民,通过这些知识来塑造这些人,它起到了塑造自由的雅典人的作用。
周绍纲:除了这些,中国的通识教育还有特别的地方吗?
高全喜:中国的通识教育和西方不一样,我们还有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孔孟之道、经史子集,五千文明从三代之治、春秋公羊学一直到近代中华民国成立之前,我们有诸多中国传统的学术。中国的传统学术一般又是以书院为主,比如阳明书院、白鹿洞书院这类渊源流长的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所以,中国搞通识教育和西方不同在于,我们还要加入一些中国传统的内容。中国传统的内容我们大体上研究了一下,开设了十多门课,有《礼记》、《孔孟》、《经学》、《公羊学》、《尚书》等等。中国传统的学术当然也有很多,经史子集等等,太多了。但我们选择最经典的,经学,如春秋公羊学,子学如孔孟之道,它们是主干。我们加入的中国思想学术的内容,跟西方的经典相匹配。所以中国通识教育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我们还要加入中国文明中的经典,这一块也是我们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中国经典还是西方经典,主要塑造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自由人格。自由人格的培养是一个丰富的、全面的、触及心灵的通识教育。这里按照韦伯的说法又包含两块,一个就是价值理性,一个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偏重于道德教育,中国很多传统的东西就是德性教育;工具理性就是15世纪以后西方的那一套。古典时期基本上是一种德性教育,偏重于美德教育、道德教育、政治德性教育,中国先秦时期的教育也偏重于这一块。到了工具理性、偏重于知识这一块时,就是15世纪以降的西学经典,它们是没有现代分科的元知识。它们与我们现在各个学院的专业知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奠定现在专业分科的基础性知识或元知识。
是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
周绍纲:北航的通识教育是怎么起步的?
高全喜:记得两年前,北航的怀校长跟我聊天,说到北航想搞个文科试验班,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培养了那么多工程师,但没有培养出一个像样的社会领域的领导者、大师,他们觉得是否可以试验试验,通过文科实验班,说不定或许能够培养一些杰出的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导人才。所以,北航搞文科试验班,搞通识教育,是基于中国社会的需要和北航人的期望。我们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设计,前两年以通识教育的核心内容为主,用学科分类来说就是文史哲为入口,政经法为出口。前两年四个学期,每个学期大致有八门课,两年不到三十门课。这些课主要介绍中国和西方的我刚才所说的几个层次的经典著作。这是我们前两年的课程,所有学生不分专业,必须把这些基本课程全学了。我们这些课程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读原著,有的一本原著很厚,未必全读完,但特别强调一定读原著;第二个是小班授课,三十个人围起来,一个老师来讲;第三个是启发式、批判式的思维。这样对讲课老师就有要求了,可以是探讨式的,并以读书笔记的方式交流。
周绍纲:这种教育模式似乎有贵族化的倾向?
高全喜: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识教育确实是奢侈的,我给校长的一封信里也写到,通识教育是有点奢侈的,或者贵族化的,北航想办通识教育,这个要考虑好,我们不能办大,大的话办不起,但办个小班北航还是有这点钱的。为什么奢侈呢?它不单是钱的投入,钱是次要的,关键是教学方式,小班教育要求大学从一年级开始,每一个学生跟老师都带有这种导师关系。我算了一下,高研院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会有十个专职的助理教授。我们设立了一个助理教授制,助理教授从学校的职称上可能也是一个副教授,但职责仍然是助理教授,我聘请其他学校的老师来作讲课教授,助理教授参与学生的讨论、课程的设置、组织学习等这一系列的活动。我算了一下,一届三十人,四届一百二十人,我有十个青年老师的话,一个老师平均下来管十二个人,一个年级下来管三个人,也就是在他手上总有十二个学生,但是这十二个学生是四个年级,一个年级只管三个。这十个老师分成不同的专业,这就等于每一个学生大学入学之后就有一个老师,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学生的导师了。除了上课跟讲课老师的探讨之外,其他时间的学习主要与高研院的助理教授发生关系,这对老师也没有太大压力,因为他只管十二个学生嘛!所以,我们本校的助理教授和学生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周绍纲:北航的文科实验班主要聘请哪些老师呢?
高全喜:聘请的老师大体上是我在北京学界的朋友,他们都很支持,我把北京、中国最好的老师请到了沙河(北航的另外一个校区)给实验班的同学们讲课。例如,搞哲学的李猛、吴飞、吴增定,他们在芝加哥、哈佛都拿到了博士学位,此外,经济学的、历史学的、国学的等都是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等国内最好大学请来的讲课老师,专门到沙河去讲一学期的课程。这样的话,我们大体上开过柏拉图的《会饮篇》和《斐德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奥古斯丁的神学著作,中国的开过《礼记》、《论语》、《尚书》,然后还开了《中国文明史》和《西方文明史》。令人高兴的是,著名的独立学者姚中秋(笔名秋风)正式成为北航高研院的教授,使我们的中学师资达到一个新高度,他开设的一系列中学经典课程影响很大。此外,我还要求同学们还要学一些理科知识,开过《科技史》把西方科技发展几个重要的阶段讲讲。还开了一门艺术鉴赏课,我们北航有个新艺术设计学院,给同学们讲艺术,带他们做陶艺什么的。主课一学期是八门,我们叫“1+1+3”模式。第一年的两个学期读中国和西方的经典。第二年,也叫读经典,但教育部要求学生毕业要拿不同的学位、修相应的学分,课程要上一些相关的专业课,我只能做一个改造,比如这学期正在讲的,题目是“经济学原理”,实际上是讲《国富论》。因为三十人到了三年级就要从三个专业中进行选择,一个是政治学(行政管理)、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法学,平均下来一个专业有十个人左右,这样三个专业就把三十人分化了,但分化也是在我高研院管理,不是分到各个学院去了。专业还是那个专业,将来拿到的是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为了经济学的课程能够达到教育部所要求的学分,二年级的课基本就叫原理课,但实际上还是经典原著选读,经济学就讲《国富论》,政治学讲洛克的《政府论》,法学讲《论法的精神》。实际上还是讲原著,但我就括弧加一个原理,将来你学法学它就并入法学的学分里去。总体来说,前两年不分专业,这些课程作为必修课,必须学。除了星期三下午没课,每周的时间基本都排满了。到了三年级之后选三个专业,法学、政治学(行政管理)、经济学,我们只能选这三个专业,这三个专业北航有博士点,另外从将来的教育资源配置来说,我们的实验班是,文史哲作为前提、导入的进口,出口是政经法这三个专业,是要经世致用,不是最后去学玄学、写小说。你可以把文史哲作为一个学术爱好,或者今后报考其他学校文史哲方面的研究生,但在我们北航,实验班的学生必须在三个专业要选一个。后边的两年,选择法学专业的,就到我们法学院去听一些课,也可能到北大、清华的法学院去修一些课,我们也承认学分。修够了学分之后将来就授予你法学学士。我们还有一个制度是,实验班三十人学完这些课之后,成绩优秀的我们百分之六十以上推荐攻读研究生,就不需要考试了。所以,第四年我也同样要求他们认真读书,因为你不需要参加研究生的考试了,除了你要考北大、清华或者其他大学,或者到国外攻读研究生,要参加相关的考试,只要你在我们本校就不需要考试。而且上研究生之后,导师可能不一定是我们学校的导师,高研院已经聘请了八位讲席教授,像周其仁、张维迎、刘东、李强、王焱、许章润、任剑涛等著名学者在我们那里带一个硕士、一个博士。现在北大那边有点问题,张维迎前两天填表的时候给我发邮件说够呛,北大有规定,北大教授不允许在外边带博士,这样就没办法了。但其他学校的老师就没有太大问题。这样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北航这个实验班有十年或者六年或者四年来陪养法学学士、经济学学士、政治学学士,这与法学院、政治学院、经济学院培养的到底哪一个真正有助于学生成才,哪一个社会更需要,哪一个能对学生以后的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这是我们高研院的一个探索,结果还有待检验。不过,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应该是我们这里的课程能给学生提供厚实的培养。两年经典著作的学习,加上人格、道德教育,还有各方面的开小灶,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会胜出的。总的来看,这个探索比较符合北航的情况,因为北航不可能搞文史哲作为同学们的专业出口,北航这方面太弱了,而且文史哲也没有相应的博士授予权。所以,北航只能搞社会科学的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培育健全的人格
周绍纲:中国高校目前已有好几种通识教育模式,您怎么看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模式?
高全喜:中山大学甘阳、刘小枫搞的通识教育,也很火,吸收了很多人。他们的优点在于看到了现在大学教育的缺陷,把通识教育和经典结合起来。他们的短板是什么呢?这两个人我很熟悉。他们特别崇尚西方的古典学,所以他们搞的通识教育偏重于纯粹的古希腊学、拉丁学这种狭义的西方古典学,他们要求三十个学生学拉丁文、希腊文,要读西方古典学的经典,这样很好,但问题在于中国人不是外国人,没有语言背景,你要把英文、拉丁文、希腊文学完再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全讲完,四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们造就的通识人才基本上变成专才了,变成了一个非常精英的古典学的专才。他们的雄心很大,我看基本是搞二十年的通识教育才可以,十年学习西方古典学的经典,再用十年搞中国的经史子集,这样才能实现他们的通识教育的伟大理想。但如果只是四、五年时间,就只能培养一批懂西方古典学、拉丁学、希腊学的专业精英,这是他们的模式的短板。而且他们反现代性,认为现代科学、15世纪以后的社会科学都是败坏的,要对现代性进行批判,通识教育要拒斥现代学术思想。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兼容,古典的好,现代的也好。他们认为古典的好,现代的败坏。这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导致的,因为他们一个是新左派,一个是极右派,不像我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我办学也是有价值理念的。总之,在通识教育方面,办学理念跟自己的价值理念、思想主张是有密切关联的。
周绍纲:北航高研院实验班的模式有什么特点?
高全喜:我只能说它是一种摸索,其特点在于它是一个理工科大学,要办文科内容的通识教育只能借助于外边的教师,但是这些老师如果只是简单请来讲讲课,没有一套通识的设计,就会很散。所以就需要一套实施通识教育的制度。中国很多文科大学现在也在纷纷改革,你学习人家的制度,到底是学习现在的北大、人大、复旦大学呢,还是学习他们改革之后的制度呢?这些就需要思考,学现在的,人家还在改呢,自己都不满意了,学未来的,未来改成什么样,谁也搞不清楚。所以北航就是在这样一个夹缝中探讨一种机制,不成熟,但基本是从文史哲入口,两年的通识教育,两年的政经法出口,将来本硕连读,然后鼓励他们攻读博士。用前两年的时间来达到刚才我所说的通识教育的目标,今后用若干年,研究生阶段学习专业知识。其实,本科后两年我也不太强调专业学习,还是通识教育,但教育部要求必须拿相应的学士,只能让他学习专业。但我个人认为,即便拿到经济学学士,你也未必掌握了多少经济学知识,还是好好把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学好,将来硕士生、博士生不愁你学不了这种专门知识,而且专门知识不难学。就像跳高、跳远、跑步似的,素质基础打好了,肯定会跳得更高、更远。所以,专业知识不要着急,先要打素质基础。到了硕士生、博士生阶段,那些专业知识现学都来得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主张。在做的时候,我可能会在课程设置上加大通识教育的力度。这是我们的模式,目前还在实验。
周绍纲:也许有人会质疑,比如说穷二代,可能会认为学了这些东西之后并不能改变命运?
高老师:这在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我觉得是这样,古希腊那是一个制度中区分了奴隶和公民,很多科学家都是奴隶,不可能成为自由民的。这是由制度区分了社会的等级。现在至少我们从制度上没有限制你想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但是现实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困境。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生,首先你要实事求是,自己的人生设计不能好高骛远。学会一些专门的知识或者谋生的手艺,这一点当然是需要的。但在这之外,并没有说不给类似的穷二代或家庭背景不好的人开辟一个空间。过去我们所谓的考试制度、选举制度,都是可以不分等级参加的。通识教育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确实有一定的基础、有现实的考量,但是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限制,限制某些人可以这样,某些人不能这样。假如你的生存压力比较大,我觉得你找一个比较现实的、正常的职业教育或者一般的专业学习是必要的。但是即使你这样的话,你要学会战胜、克服自己,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为自己今后的提高阅读一些东西。大学确实是一个职业导向的东西,但你不能把你人生的东西都穷尽在这里头。所以我觉得生存状况比较差的人要实事求是,不能好高骛远,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在大学把人生穷尽,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任何一个专业,即使通识教育的专业,你只要能够学下来,未必就不能找到工作。比如一些学校想聘请文史哲专业的年轻的好的老师,就找不到。并不是学了文史哲就不可能就业,实际上专业就业的途径是很狭窄的,但具备一定的综合性知识,真正的有自由人格或有能力,反而就业前景要远远大于一些有手艺的人的前景。这方面很多家长有一个误区,说上大学必须学一个专业,不学专业就找不到工作了。但你们如果接触那种高层次的职业经理,或者大的企业、公司,或者公务员的系统,我以前有些学生从事这些工作,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不太看你是经济学院的、法学院的还是文学院的,主要看的还是你的能力。通识教育就是要塑造你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通识教育塑造出来的人才反而比专业人才在社会中的适应性更强。我经常对我们实验班三十人说,别着急,我相信你们将来肯定不会找不到工作。人大国学院的毕业生工作都好找,何况他们还不是通识教育。所以这个问题首先在于你个人无论是出于贫困之家还是官宦之家,自己要人格健全,要有一种不要靠家庭的意识,要自立。通识教育就是塑造这方面的能力和认知,这是最关键的。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1962年10月生。哲学博士(师从贺麟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宪政理论。曾在海内外出版的有关中国思想、西方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学术专著有:《理心之间——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休谟的政治哲学》,《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另发表论文《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论国家利益》,《论民族主义》,《论“宪法政治”》,《立宪时刻》等。主编有:《大观》,《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等。